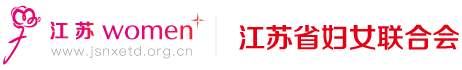我的小孙子思齐尚未学语时,有两样爱物,小汽车与小人书。每天刚起床,他就从自己的小书架上找到绘本,点着小碎步送到我手中,一页一页掀开,让我读给他听。每读一页,他都“嗯,嗯”点头应答,似乎已完全听懂了所读的意思。
我随意翻开一页,问他:“小松鼠在哪里?”他立马伸出小手一指。我又问:“小青蛙在哪里?”他又用手指着书上的青蛙图案,睁着亮亮的大眼睛看着我,听到我一声“对啦!”的赞赏,便抿着嘴得意地一笑,显得很害羞的样子。我又趁机考一考他:“小青蛙怎么叫的?”“呱呱——”;“小汽车怎么叫的?”“滴滴——”……每次回答之后,他都会很陶醉地眯一下眼睛,好像在说:“我答对啦!”
思齐就是从书本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的,他迷上小汽车,也是从书本开始的。他有四本关于车的书,可以说百看不厌,让我读了一遍又一遍。读了书,他就去玩大大小小的玩具车。由喜欢方向盘,到乐见圆形的东西,每每遇到,他都要走近转动几下,摆弄一番。周末去郊游的时候,他会朝每一辆过往的汽车行注目礼,小手不停地指指点点。
到了断乳期,他妈妈耐心地给他读绘本《再见,妈妈的奶》:“长颈鹿很喜欢吃妈妈的奶,但是,它现在能吃很多树叶。它和妈妈的奶说‘再见’!小兔子很喜欢吃妈妈的奶,但是,它现在能吃很多胡萝卜。它和妈妈的奶说‘再见’!赵思齐也喜欢吃妈妈的奶,但是,思齐现在能吃很多饭。思齐要和妈妈的奶说‘再见’!”很显然,关于孙子的这一句是儿媳妇加上的。孙子听得很认真,应该是听懂了,就真的和妈妈的奶说“再见”了,没有别的孩子断奶时的激烈反应。
随着牙牙学语,小书架日益增高,孙子的小脑袋里渐渐装满“十万个是什么”。走过停放的车辆,他总要追问,“这是什么标识的呀?”“这是什么国家生产的呀?”;走过一处花坛,他总要指指点点,“这是什么花呀?”“这是什么图案呀?”;来到运动场,他摸着那些健身器材,“这是什么形状的呀?”“这是什么运动的呀?”;看到天上的月亮,他的问话更奇特,“月亮是什么味道的呀?”“月亮的家是什么地方呀?”……这些好奇的“是什么?”得到了解答,他才会回以灿烂的微笑,有时还亲热地和我贴脸:“爷爷,我爱你!”
孙子是伴着“每天三分钟”(听读播放器)起床的。每当这个时候,他显得很兴奋,或手之舞之足之蹈之,或用稚嫩的童音有节奏地诵读着:“云对雨,雪对风,晚照对晴空。来鸿对去燕,宿鸟对鸣虫。三尺剑,六钧弓,岭北对江东。人间清暑殿,天上广寒宫。两岸晓烟杨柳绿,一园春雨杏花红。两鬓风霜,途次早行之客;一蓑烟雨,溪边晚钓之翁……”这是清人车万育的《声律启蒙》。
正在我一边惊叹一边竖起大拇指点赞的时候,他的“是什么?”又来了:爷爷,“晚照”是什么呀?“来鸿”是什么呀?“广寒宫”是什么呀?“颜巷陋”是什么呀?……
好在我这个站了四十多年讲台的爷爷,还勉强对付得了这些“是什么?”,还能给他解释到不再追问“是什么?”。我暗自庆幸,小孙子还是给爷爷留足了面子,没让爷爷被“是什么?”折腾到崩溃。
看来,作为爷爷,我还得做足应对孙子“是什么?”的功课。
趁孙子午休的时候,我浏览了孙子的专用书架,真的有点眼花缭乱:中国经典动画大全集,探索频道·万物由来的秘密丛书,根据荷兰的马克斯·维尔修斯童话改编的“青蛙弗洛格的成长故事”系列,被誉为“最亲切的数学概念启蒙图画书”的“你好,数学!”系列,日本超人气绘本作家宫西达也的“狼与小猪”系列……这些幼儿书有中文的,也有外文的,大大小小薄薄厚厚应该有几百本吧。可以想见,它们催生的N个“是什么?”,肯定会让我这个“偏科”的爷爷目瞪口呆、无以应对。
这不,孙子在听读一本书上听到“请勿打扰”时,立马仰头问我:“爷爷,‘请勿打扰’是什么呀?”我告诉他:“就是别人工作和休息的时候,你不要扰乱别人。”他又仰头问:“‘扰乱’是什么呀?”我答道:“就是打扰啊!”孙子以疑惑的眼神看着我,似乎在说:“爷爷,你绕了一圈怎么又绕回来了呀!”我自己也暗笑,往往最简单的“是什么”,也最难弄得既了然于心又了然于口。
晚上,孙子又照例听他爸爸妈妈读绘本,《和爸爸一起读书》,美国人理查德·乔根森写作、瓦伦·汉森绘图的。“我关灯时,爸爸轻轻地说:‘每天晚上睡觉前,一定要读一本书。’我一生最美好的记忆,就是和爸爸一起读书。”孙子赶紧问:“爸爸妈妈,什么是‘最美好的记忆’呀?”
哈哈,我的书虫小孙子,又在拿“是什么”考验他的爸爸妈妈了!
这两年,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皖西老家,每次网络视频都见到已上幼儿园的孙子端坐在高高的书架下,神情专注地读他自己的书,他还和他妈妈在网络社交平台创办了“齐思妙想读绘本”公众号。我高声赞一声“小书虫!”,他把脸从书页移向手机镜头,咧嘴一笑,眨一眨眼:“爷爷,老书虫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