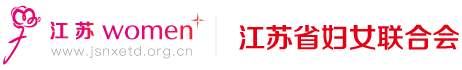峰峦如聚,烟波如怒,花亭湖是山的世界,是水的世界,更是山河与共、水天相连的世界。它位于安徽省太湖县境内,1990年,赵朴初先生归乡游湖时,赞美花亭湖“千重山色,万顷波光”,果真熨帖。
车子沿着花亭湖的湖堤盘旋疾驰,烟云湖水渐渐隐退,古寨就横空出现了。
古寨沿河而建,水皆缥碧,清澈见底,河底细沙,粒粒可数,真令人赏心悦目。
有河焉得无桥?寨口的桥,大条石一块块垒成,如虹卧波,传说是寨中胡氏先人领着五个儿子建成,因而唤作五福桥。百年即逝,桥姿雄健如初,建桥的人不知哪去了。或许彼时,骄阳如火,他们成群结队,肩抬巨石,步履蹒跚,号声震谷,青筋暴起的额头正汗落如雨……
河中多石,大者如狮,如象,如牛,如山丘,如宝船;小者如鹤,如龟,如兔,如蛤蟆,如螃蟹。每一块石头,皆经受了岁月与河水的浸润、磨洗,静默得像一尊尊修行的菩萨。五福桥两头的桥基,皆依河就势,建在牛背宽厚的巨石上,虽历经数百年风霜雨雪,行人往来,却愈显厚朴,牢固,从容。
走进村子,恍如走进一个遗落许久的世界,黑瓦的旧民居,石板的小路,雕梁画栋,马头墙,触目皆是。许多民居的廊檐上,门框上,精美的木雕,绚丽的彩绘,空灵的壁画,皆依稀可见。古寨昔日的繁华富庶,人来人往的热闹场景,犹在眼前。
行走间,远处山坳漾来一片暮霭,天陡然暗了,寨里远远近近升起了炊烟。暮色下的炊烟,一缕缕,荡悠悠,心头忽被揪扯了一下,故乡红砖瓦屋的平房就出现了。少年的我在暮色里疯跑,年轻的母亲站在黑瓦的檐下,双手拢在嘴边,大声唤我小名。
循着炊烟走进一个院子,一只黄色小狗朝我汪汪两声,又摇着尾巴跑远。几个妇女正在厨房里忙活,熊熊灶火映红了她们和善的脸,锅已烧红,一个大姐拿起一段旧丝瓜瓤蘸了蘸碗里的香油,手腕一翻,已在锅里画出一道圆圈,嗞一声响,瞬时香气四溢,趁滚热的香油还在锅面发愣,大姐抄起木勺,盆里舀了半勺浆水,手腕一抖,嗞——,又一声响,一个淡黄的同心圆已出现在锅里。大姐是个巧手,才放木勺,一枚亮晶晶的蚌壳又被她抢在手里,蚌壳轻轻一旋,一张厚薄均匀的面饼就成形了。
做的是什么?我看得发呆。
豆粑呀!大姐笑道,见闯进个陌生人,她一点儿也不觉得唐突。
大姐嘴里笑着,手可没停,蚌壳轻轻一划,整张豆饼应手而起,扔在一旁的竹筲箕里,那里面已叠了几十张豆粑饼了。
切成丝,晒干,炒着吃,烧火锅都成。几个大姐笑嘻嘻地介绍。
夜宿龙潭山舍,一个有回廊、有天井、有堂轩,布局精巧的古民居,也吃上了入口软糯、越嚼越筋道的豆粑。民间畅行的小吃,无不凝聚着先人的汗水和智慧,吃起来别有风味。
古寨的夜太静,风声,水声,说话声,鸡鸣狗吠声,皆不可闻,无边的黑暗,静得时间似已停止运转;古寨的夜太短,短得猝不及防,脑袋才挨上枕头,天便亮了。
悄然出门,沿河而上,河水斗折蛇行、幽深无尽,两岸参差分布着一块块坡地,地像河里的石头,形状各异,地里的萝卜、白菜、大蒜,青扑扑,油嫩嫩,水灵灵的。灵山秀水间生长的草木、菜蔬,自有一股丰容。
两边的山越来越高,山上的槭树、枫香、乌桕,窑火一样红艳。古寨的晨风,水一样清冽,晨风轻吻,树儿的枝叶摇动,整座山谷皆染红了,皆沉醉了。
河边一户人家的门前,突然飙起一道浓浓的炊烟,走近看时,却是一个汉子正在烧水。屋檐下,整齐的棒子柴码得比人还高。烧水用的还是我幼时常见的水催子,长长的壶嘴,身子中间,一个圆柱的孔洞,棒子柴烧得毕剥作响。
与汉子攀谈,说姓胡,是古寨胡氏一世祖的后人。说起先人的辉煌过往,汉子一脸荣光,努着嘴:喏,你再往上走,看看我们胡氏宗祠,那匾额可是当年的南京总督张柏林赠送的。现在虽说有些破败,那时可洋货得很,光是房子,就分为前堂、后堂、东厢、西厢、天窗、地池、过廊、门厅。我们祠堂的石头上,雕的是奇花异草、飞禽走兽;砖头上,雕的是楼台亭阁、人物戏文,哎,那才叫一个排场……
汉子所言无虚,我看到的胡氏宗祠、胡百万故居,内部的砖石、门窗、梁柱,的确还有当年雕龙画凤、富丽堂皇的气势。不仅如此,整座古寨里的二十余幢明清民居,其门楼、巷道、水系皆布局合理,暗合枕山、环水、面屏的朴素风水理念,古寨历尽沧桑而丰韵犹存,或许也得益于这人与自然和美安居的古朴风尚。
胡百万故居门前有一潭,潭水如镜,深不可测,因自远山而来,其形如龙,故而这河便叫了龙潭河,这寨也便叫了龙潭古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