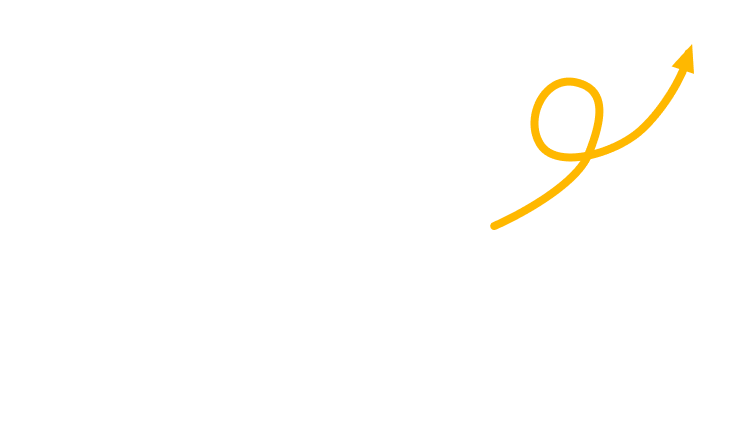人生处处有境界
蔡明
2025年全国高考语文二卷里,宋之问与陈子昂的题画鹤诗,像两帧泛黄的绢本,托着初唐文人的精神剪影在时光里浮动。初读宋之问《咏省壁画鹤》“鶱飞竟不去,当是恋恩波”,只觉笔锋裹着宫墙的掠影,依附、效忠、颂圣的意味,顺着诗句便自然溢出。可这“思想”哪有“境界”可言?再细想,那欲飞还留的鹤,又仿佛戴着镣铐起舞。“当是”二字,藏着多少揣摩?“恋恩波”的温顺背后,或许是“昂藏真气”“鶱飞难去”的本能与现实的角力。忽然读懂那些颤动的鹤羽:不是对樊笼的屈从,而是在禁锢中保持羽翼完整的隐忍。这种“笔下岁月,骨里孤寒”的撕裂感,恰是境界的真容——它从不在完美的飞翔中显形,偏在折翼的挣扎里闪露锋芒。
陈子昂笔下的画鹤却挣脱了所有羁绊。“古壁仙人画,丹青尚有文”起笔便带仙气,“独舞纷如雪,孤飞暧似云”更让墨痕有了魂魄。那鹤抖落的岂止是翎羽,分明是“自矜彩色重,宁忆故池群”的自嘲里的不忘初心,仿佛能听见羽翼划破暮云时,泻出一串“江海联翩”的长鸣。宋之问的鹤在画框里困于得失计较,羽翼间总带着几分仕途的牵绊,而陈子昂的鹤早已把目光投向绢素之外的苍茫。“自矜彩色重”看似夸耀羽翼华美,实则藏着对世俗评价的清醒反讽——即便被赞“彩色重”,也从未忘记故池的自由本真。高考题让学生比较二者境界,实则是在叩问:这两种鹤的姿态,恰似生命面对局限的两种选择:是耽于皇权的金丝笼,做依附权贵的八哥,还是挣脱世俗的画框,做直面苍茫的孤鸿?
这种关于“局限与突破”的境界追问,在作家韩丽晴的散文《境界》里的人物设计师小蔡身上,有了最朴素的注脚。雨天的工作室里,他用老烟斗改造的吹火筒引燃核桃炭,红泥小炉上的陶壶渐渐吟出沸水的轻响。泡茶时“拇指与中指轻捏壶柄,食指稍按壶盖”,手腕微旋间茶水已注满茶杯,桌上竟无半滴遗痕。他说“把心放平,沉下来,都能听得懂万物的语言”——对茶器的敬畏,对水火的恭谨,全藏在这不动声色的拿捏里。案边那只青段泥茶叶罐,他盯着底部突起的线条较真:“比图纸宽了半毫米,糙了。” 这半毫米的执着里,藏着的是对“至善至美”的信仰,正如他镜头下的草木,能拍出“树木的呼吸与欢欣”,这种对本真的洞悉,让喧嚣行业里的静气有了重量。
作家韩丽晴恰似一位隐匿于烟火人间的观察者,以细腻且悲悯的笔触,在生活的褶皱里探寻哲学与艺术的真意。她的散文集《寻意古南街》,宛如一面澄澈的镜子,映照出平凡紫砂艺人的精神世界。在这部作品中,韩丽晴并未着眼于宏大叙事,而是俯身于琐碎日常,去捕捉那被众人忽视的“内心里些微的光”。她从不混迹江湖,宁愿深入古南街,与普通匠人对话,从他们对紫砂工艺的坚守中,体悟到一种对抗浮躁、回归本真的力量。这种对平凡生活的珍视,实则蕴含着对生命本质的追问——在物质至上、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,如何才能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安适?韩丽晴以这些匠人的故事给出答案:专注、热爱、坚守,在一器一物的打磨中,完成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;境界并非超凡脱俗的遥不可及,设计师,制陶人,每一个平凡人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,芸芸众生共同构成了这个丰富多元的境界。
作家是精神产品的制造者,韩丽晴的文字隽永、考究,每一句都似精心打磨的玉器,温润而有质感。描写壶在高温下的窑变时,她写道“窑变令壶上落满似明似暗的光斑,如散落在夜空的星星,在无尽浩渺之间闪烁。那光不起眼,甚至微弱,但每个光斑又是那样倔强,似穿透千年冰土,奔腾而来,固执地亮着”,这般灵动且充满诗意的语言,将原本静态的器物赋予了生命的律动,让读者仿若亲眼看见砂器在火与土的交融中重生。她还善于从寻常事物中提炼出独特的审美体验,像从江南春景中最嫩的那抹绿里,领悟到江南人“以小为美”对物欲的抵制,在“道”与“器”之间搭建起一座诗意的桥梁,让艺术从生活的土壤里自然生长,绽放出别样的光彩。
从盐阜大地到苏南小城又至淮北平原,我与学生的“黑板约定”总在晨光里苏醒:左侧每日赠言生长着思想的嫩芽,右侧每日一诗流淌着审美的清泉,写作流程从初作到重作如星辰轨迹般清晰,孩子们在互批中碰撞火花,争执不下时我便化作一阵三言两语的“穿堂风”。学生总说记得我用彩色粉笔放大他们的进步,那些方正的笔画在黑板上舒展成羽翼时,我眼里始终有着光。让语文从课本里走出来,让生活往文字里走进去,这两种脚步踏响的,正是教室窗外的春华秋实。语文教学的境界原是这般:从纸页间出发,往烟火处行走,最终生长为生命本身。
当乡村教师接过那本教龄满30年的红色烫金“荣誉证书”——那由教育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颁发、印着神圣国徽的见证,总让我想起自己的“特龄”也已悄然走过30载。即便岁月流转,我对课堂的眷恋丝毫未减,始终愿做三尺讲台前的常客,以“永远的读者”“终身的学习者”“乐此不疲的生态教育实践者”自勉。
每日清晨,读书是雷打不动的晨课;白日里,独立解读文本是必修的日课;夜深人静时,坚持写作是深耕的夜课。而让每个孩子都能触摸到语文的脉搏,则是刻在骨头上的终生课题。课堂之上,无论谁起身发言,我都渴望拨开言语的枝叶,看见底下藏着的灵气与努力。
我仍坚守着心中的教育生态:用赠言为学生播撒暖光,用古诗浸润他们的心田,用微笑传递成长的底气,用生态读写做知行合一的示范。就像韩丽晴笔下的小蔡,在茶叶罐的半毫米间较真,于无声处敬畏万物,我也始终为每个需要成长的青年教师量身定制培育方案。个人以为,领衔人的境界从不是一个人的光芒万丈,而是一群人的彼此照亮。
诗人的境界,作家的境界,匠人的境界,又想到笔者曾经写过的家长的境界。冯友兰的 “四境说”便有了具象的注解:把孩子宠成温室宠物的“自然境界”,看似慈爱实则是生命的囚笼;为分数不择手段的“功利境界”,如同给幼苗猛施化肥,根基终会虚浮。而诸葛亮《诫子书》里“静以修身,俭以养德”的嘱托,恰是“道德境界”的范本——那位临终前仍叮嘱儿子“非宁静无以致远”的父亲,懂得教育不是雕刻而是浇灌,不是灌输而是唤醒。就像那位高考失利后对孩子说“你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”的母亲,她的境界里,有比分数更辽阔的天空。
教师节前夕,桂香漫过窗棂时忽然又悟:教育的境界不在烫金的奖状里,而在小蔡打磨砂器的掌心温度里,在陈子昂笔下鹤鸣穿云的孤高中(那是突破局限的勇气),在宋之问画中鹤羽颤动的隐忍里(那是困守中的坚守)。它藏在千万教师的日常里:晨读课上带着沙哑的范读,像老树枝头的第一声鸟鸣;作业本上红笔圈点的温度,能焐热少年眼底的迷茫;办公室深夜亮着的那盏灯,把备课的影子投在墙上,忽长忽短,像在丈量光阴。他们或许成不了史册里的传奇,却用无数个45分钟,把“立德树人”的种子种进时光的土壤。
就像宋之问的鹤终会冲破画壁,陈子昂的鹤永远望着青天,这些有境界的教育者,正领着孩子们在时代长河里行船——既守得住船底的三尺讲台,也望得见船头的万里山河。这该是教师节最好的献礼:以凡人之境做舟,载育人之境为帆,与时代同频,赴山海远阔。
 分享
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