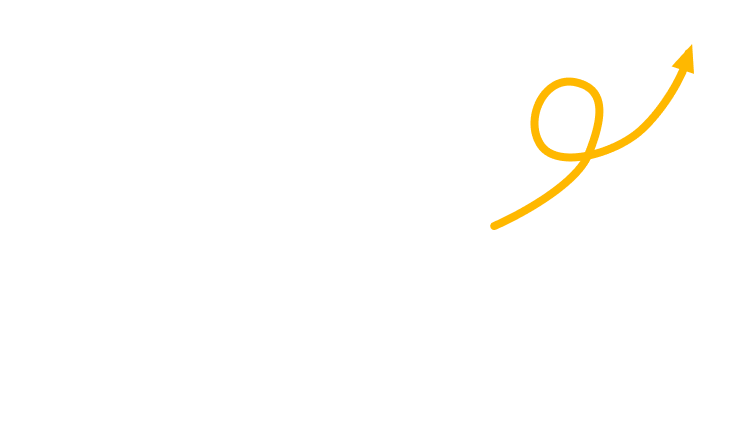外婆的文学课
苏阅涵

我的外婆不识字。她的手掌心布满纵横的裂纹,能精准地掂量出盐分的多寡,却断然是捏不住一管轻飘飘的毛笔的。但我总认为,我的外婆是一个文学家。
她的课堂,不在书斋,在厨房。
那是一个冬日的黄昏,窗外是凝滞的、铅灰色的冷。屋子里却很温暖,灶上的瓦钵里“咕嘟咕嘟”炖着一锅胡萝卜,水汽氤氲而上,在玻璃窗上涂出一片迷离的雾。外婆坐在一张小凳上,就着灶膛里温存的火光,不紧不慢地剥着一颗柚子。那柚子皮极厚,她枯瘦的手指探进去,费力地,却又极有耐心地,将它一整片完整地剥下来。
她将一瓣剥得干干净净的柚肉递给我,然后拾起地上的柚皮,凑到鼻尖深深地一嗅,眯着眼说:“你闻闻,这像不像古时候那些读书人点的香?”
我接过那柚皮。它的香气,不似花香那般甜媚,也不同檀香那般沉肃,它是一种清新的、冷冽的芬芳,带着植物特有的涩意,直透脑髓,让人精神为之一振。是啊,古人所谓的“红袖添香”,添的或许未必是名贵的麝与檀,而是这一份于清苦中寻得雅趣的心境。外婆不识字,却用一颗柚子,让我嗅到了文学的味道。
她的课堂,还在地里。
收番薯的时节,我跟在她身后,看她用一柄小小的四齿耙,小心翼翼地探进土里,再轻轻一撬,那紫红色的番薯,便从松软的、黝黑的泥土中被“请”了出来。它们沾着湿泥,带着地气,沉甸甸的,有一种朴拙的欢喜。
外婆拿起一个,用粗糙的手掌抹去上面的泥土,眼里有一种收获的、满足的光。“你看,”她说,“这东西,长在土里,不起眼。可它顶饿,养人。”
她又拿起另一个,形状有些滑稽,弯弯扭扭的,像个蜷缩的兽。“这个长得丑,”她笑了笑,并不嫌弃,“可你尝尝,说不定比那些光溜溜的还甜。写人写事,有时候,你们老师教你们写作文,就要写这些丑的,才真,才记得住。”外婆,这个泥土一样的老人,用最朴素的劳作告诉我,文学的本质,是向下扎根,是供养生命,是拥抱那些不完美的、真实的形态。它不必是花瓶里精致却无用的花,它更应该是土里的番薯,带着泥土的气息,却能实实在在地喂饱人的精神。
外婆从不说教,只是在她那个由具体事物构成的世界里,信手拈来地,为我指认那些抽象概念的本来面目。
她会指着一场雨后,墙角悄然生出的、滑腻的青苔,说:“瞧,这就是生机。”她会在月明星稀的夜晚,摇着蒲扇,望着深邃的天空,喃喃自语:“今夜的月亮,像一块被擦过的旧银元。”我上初中时有一次考试失利非常沮丧,她递给我一碗新熬的姜糖水,说:“喝下去,肚里暖了,心就定了。这就是力量。”
许多年后,当我真正开始阅读那些浩如烟海的典籍,我才在后知后觉中,一次次地与外婆的课堂重逢。读《诗经》,“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,那不就是外婆口中依着节气过活的具体的生活么?读张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,“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”,那份于天地苍茫间对美的追寻,其内核,与外婆深嗅柚皮之香的雅致何其相似。
如今,我也到了能够体会人生况味的年纪。每当我在书斋里感到疲惫或空虚时,便会闭上眼,回到外婆那间被水汽与香气笼罩的厨房。她静静地坐在那里,理着柴火,或是搅动着一锅粥。灶膛里的火光,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温柔地跳跃。万卷书,万里路,似乎都融汇于她那清澈而深邃的眼神里。
我的外婆不识字,可她本身就是一部鲜活的文学,教会我很多。
 分享
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