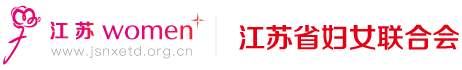我第一次听到滚花生,是在十多年前。
秋天一来,年逾古稀的婆婆就会帮人锄花生。收工回家前,婆婆会在收过花生的田里,再刨上一会儿。
回到家,婆婆拿出几斤花生说:“这是我滚来的花生,等下煮起来吃。”这些花生,是遗留在田野的小个子,长得瘦弱,典型的营养不良。把它们清洗干净,连着外壳煮起来吃,有的没有果仁,只有白花花的一层皮儿;有的里面是黑的,像被蛀蚀的牙齿;有的带着细长的尾巴,一看就是个淘气鬼。当然,大部分是可以下嘴的。花生仁细细的,粉白色,一咬,带着清甜的香。
吃着婆婆滚来的花生,我总是试图去拼凑婆婆滚花生的情形:没有风,田野上滋滋地冒着热气。一个老人,正以老树的姿势,向土地俯下身子。夕阳将她的影子拓在粗糙的大地上。我看到了另一种明亮,那是刚强和柔软迸发出来的明亮。
后来,婆婆开始自己种花生。她常常变戏法似的带回一大捧花生,有叶有秆有根,甚至还带着一些泥土。婆婆在水门汀地上摘花生,我也坐在她身边摘花生。一颗、两颗,一把、两把,花生落在一旁的竹篮里,发出脆脆的声响,像家门口的指甲花,奔跑出一地素淡的美好。
在我成长的记忆里,吃花生是一种奢望。整个村庄,没有一家种花生。每一块土地,不是种青菜、萝卜、豆角,就是种稻谷、小麦、红薯。在那个温饱还悬在半空的年代,谁会去种花生这样奢侈的作物呢?有一家也许经不住小孩的恳求,选了一块泥沙地种了一畦花生。这一畦花生,从种下去开始,就被一群狼一样的小孩盯上了。花生还没有成熟,就被拔光了。光秃秃的土地就如被拔光了羽毛的鸟,赤裸裸地展示着那个年代的贫寒和苦涩。
那时,谁会想到几年后,会家家户户种花生呢?
自己家种花生后,婆婆依然习惯滚花生。婆婆当了一辈子的农民,十四岁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,作为土地忠诚的守护者,她对所有的粮食和果实,有着近乎偏执的爱。有一次,婆婆还把老鼠抢走的花生给抢了回来。
那次,婆婆无意中发现有一个地方泥土特别光滑,还泛着白光。
婆婆猜想那是一个老鼠洞。老鼠爬进爬出,改变了泥土表面的形态。婆婆像地下工作者一样,带着一份隐秘的想法,追着洞挖,没多久就挖到了老鼠的粮库。“你看,足足有五斤呢。”婆婆笑着,那把忠诚的老锄头,叩击着泥土,发出“叮叮咚咚”的声响,仿佛是胜利的号角。
如今,八十五岁的婆婆不仅有高血脂,还得了阿尔茨海默病。她像个果敢的智者,把大部分往事抛弃在时光的山沟里。
一个偶然的机会,得知花生芽老少皆宜,脂肪含量低,维生素含量高,白藜芦醇的含量是花生仁的一百倍,我决心做一道花生芽。
花生有粉皮和红皮两种,做花生芽,粉皮花生是首选。把花生剥离果壳,是一项手指运动。右手大拇指和食指用力一按,花生啪的一声,裂了口,再用两个大拇指一掰,花生仁就出生了。它们往往以双胞胎的画风登场,小耳朵一样的果壳,摇篮一般接纳着胖乎乎的花生宝宝。偶尔,摇篮养育出单胞胎或三胞胎。有的花生宝宝胖乎乎的,撑得摇篮没有一丝空隙;有的瘦不拉几的,不用太使力,果壳就破了。挑出外衣破的、果肉瘦成枸杞干的,颜色变灰、变黑的舍弃或干吃,其他的选一部分泡在清水里。
发了芽的花生,宛如一只只长嘴鸟,在欢快地唱着歌;有的花生芽努力地往淘米篮的洞外钻,仿佛倒生了一片玉色的丛林。发了芽的花生慢慢脱掉粉色的外衣,露出玉黄色。
把腊肉切成薄片,和辣椒、生姜一起炒出香味后,倒入花生芽。出锅前加点葱花。不喜欢吃脆的,可以将花生芽放高压锅里煮上两分钟后再炒。
“好吃吗?”我把花生芽端到婆婆面前,弯着身子等待婆婆的评价。其实,我知道婆婆不会和以前一样,乐呵呵地说:“好吃好吃。”如今的婆婆,成了一颗老去的花生,每天蜷缩在自己的摇篮里,不愿意苏醒。
“好吃吗?”我再次问婆婆。婆婆笑了。“呵呵,呵呵。”两个“呵呵”之间,是毫无内容的空洞。
婆婆把自己丢了,但透过时光的镜片,我又一次看到了婆婆滚花生的情形。